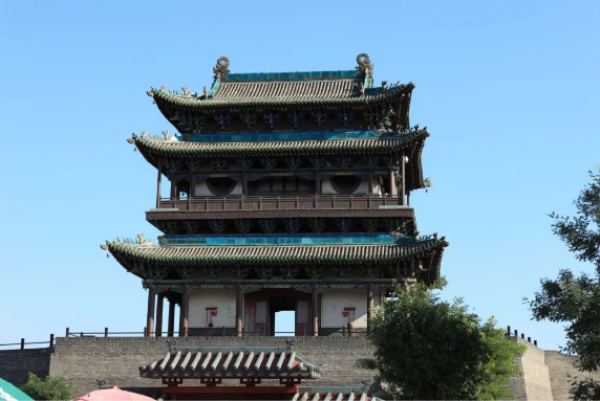近日,“世界史不是历史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不是中国语言文学”等“白马非马”的荒诞剧不断上演,令人哭笑不得却又引人深思。这是相关工作人员的孤陋寡闻?还是故意刁难?看似是当事人谨慎认真、恪守制度的责任之心,实则是怕麻烦、不担当的推诿做法,一种不知变通的官僚作风。

为官者自是要慎用权力,但要心中有“人”,不以人为本,慎用就成了不作为的“懒政”。于书画者而言,为艺治学也要讲究“慎”字,这既是对传统文化的敬畏之心,也是一种治学的方法和为艺的态度。
30年前,沙孟海先生出版作品集时,坚持要把出版社初定的书名《沙孟海法书集》中“法书”一词改成“书法”;无独有偶,谢稚柳先生在20年前出版作品集时,执意要删去《谢稚柳书法集》书名中的“法”字,而叫“书集”。两位老先生的一字之改,绝非一般意义上的咬文嚼字,或是故作矫情,而是谦虚谨慎、实事求是的治学态度,是对艺术的虔诚之心使然,也是大家风范的彰显。回过头来看看时下,如此谦慎者少之又少,而喜戴高帽者如蚁附膻,借着书画家的帽子逐名追利,早已忘却心正则笔正,哪里还能做到“君子必慎其独也”。由此看来,沙、谢二老的一字之改不啻是一剂针砭时弊的良药。
书画者当以“慎”来要求自己,慎是一种责任,也是一种能力。明大臣王锡爵权高位重,于书法也有很深的造诣,然其不以书立身,而以社稷为重,这是“慎权”;人前人后一个样,私底下、无人时也能不放纵、不越轨、不逾矩,这是“慎独”;小事当慎,小节当拘,细微之处见品德,这是“慎微”;言为心声,书为心画,内心无私欲方可无虞,这是“慎欲”;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择友分良莠,这是“慎友”。慎者才能不为名所累,不为利所困,克己除私欲,加强自我修养、提升境界,至纯至真地为学为艺。
凡事皆有度。过“慎”者就会缩手缩脚,无绳自缚,在学画过程中往往流于时弊,是知有古而不知有我,徒知学古人而不知学古人所师造化,焉能内得心源?过慎者往往囿于自己的世界中,既不行万里路也不读万卷书,只会老鼠磨牙般地摹写,甚至抄袭,这样的作品以多产、高价、易售为目的,故而一改初心,只能随波逐流、迎合世俗。
慎不及者,视艺术如儿戏,不曾“傍窥尺牍,俯习寸阴”,只会“引班超以为辞,援项籍而自满”,任笔为体,聚墨成形。或是曲解“笔墨当随时代”,强借当代艺术之名玩起杂耍式、概念化的“创新”,要么低级无趣流于鄙俗,要么粗疏简易近似狂怪,皆悖于理法,流于江湖,都是野狐禅,邪魔歪道。对艺术不慎者自是难有敬畏之心,浮于表面,流于形式,只会哗众取宠、忽悠众人,艺如其人,这样的人又能走多远?
书画者当“慎”且慎者有度,不偏不倚、不激不厉,方可不偏离为人、为学、为艺之道。
 手机版|
手机版|

 二维码|
二维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