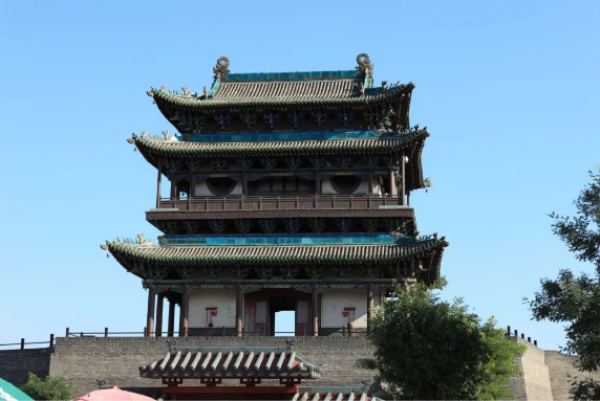当我们谈论20世纪中国美术史、谈论长安画派时,我们回避不了赵望云先生。这种艺术史上无可回避,也无法回避的事实本身,就是我们今天依旧谈论赵望云的第一意义。
之所以如此,当然是因为赵望云为中国艺术的发展做出了以下贡献:第一,今人所做当代中国画发展史讨论20世纪中国画发展时,指认了三条发展道路。延续传统型,代表人物齐白石、黄宾虹;引西开中型,代表人物徐悲鸿、蒋兆和;走向现代型,代表人物吴大羽、林风眠。但是,以赵望云为代表的走向民间的写生之路,并由此开宗立派的第四条道路,却被整体忽略。应该知道,赵望云及其奠基的长安画派,引领了新中国绘画于20世纪60年代在西北地区的崛起。第二,清代以前的传统绘画基本忽略西北地区的人文自然。而赵望云及其奠基的长安画派,使得西北人文自然第一次成为中国画,尤其是新中国绘画主要表现题材。我们今天看到的大量关于西北人文自然的所谓“西北风”绘画,都应归功赵望云及其长安画派。当然,也有其他画家比较早地来西北地区写生创作,韩乐然、张大千、董希文等都是开先河者。但是,由于各种原因,他们都没能在西北地区持之以恒,而是蜻蜓点水,采风式体验。第三,赵望云是中国绘画史上,最成功地挖掘了农民潜能的艺术家。他的挖掘,不是仰视,也不是俯视,而是身在其中的亲近。第四,作为艺术家,他还是我国文保事业的先驱。1950年,他以西北文化部文物处长的身份负责接管敦煌文物研究所;1952年,国家首次勘测炳灵寺,赵望云是团长。团员则有常书鸿、吴作人、张仃、李可染、段文杰。第五,在作品人民性方面,无出其右者。中国绘画史上,最应该被称作“人民艺术家”的应该是赵望云。我们知道,齐白石一直被称作“人民艺术家”。但我认为赵望云更应具备这一称号。1936年,盛成先生在赵望云画集序文中一句话,很有洞见。他说:“白石翁画中有物,不爱摹古,望云画中有事,更进一步,而且这个事就是这个时代的事又是这个世界的事。”第六,在教导学生、传承中国艺术方面,他所具备的“酵母”意义,也是20世纪大师级艺术家中少有的。比如,绘画方面,他的学生黄胄、方济众、徐庶之等,都名重一时。子女中,长子赵振霄是新加坡国家乐团首席大提琴手,三子赵振川是知名画家,四子赵季平是知名音乐家,等等。
这些,在我本人所写的有关赵望云的文章中,都有论述,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看看。但今天,我想谈论以往赵望云研究中,大家没有谈到的一个话题: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艺术创作的内在里路,是否还有新的途径?
毋庸置疑的是,国家,尤其是新中国的新气象,一直是长安画派以及那个时代艺术家普遍的艺术母题。赵望云的创作中,当然也不例外。但是,国家主题之外,属于农业文明的自然时间,成了赵望云创作中一个不容忽视的方面。他的自然时间在相对循环、封闭的西北空间,获得了传统诗学“与物为春”的精神拥抱。他作品中独有的那份发自肺腑也发自大地的温暖慈爱,是中国自然诗学一直置顶的审美维度:朴实、善良、慈悲、温暖。赵望云的作品中,不是没有西北画家常有的苦涩,而是他关注的重点不在于苦涩,而在于苦而回甘。苦而回甘中,赵望云的作品具备了持久的审美品质。这个品质说白了就是司空图《诗品》中的“自然”:俯拾即是,不取诸邻;与道俱往,着手成春。
还有人说,黄宾虹那样的艺术家有着完整的笔墨体系,比如他总结的“五笔七墨”,但赵望云这方面略显不足。某种程度上说,此言不虚。但是,赵望云来自骨子里的特有的那种醇厚的笔墨意味是任何固有的体系套不住的,它就来自于生活与生命本身。有一点必须明了:黄宾虹的笔墨,很多人都能学,也能学会,因为他来自于既往的技术体系,但赵望云的笔墨意味和既有的技术体系有关,却不完全如彼。他晚年笔墨中那种“和谁都不争,和谁争也不屑”特有的温暖慈悲,是别人想学也学不来的。
此外,现在很多人说,当下艺术创作中,有高原,没高峰。其实,当一个高原具备了相当高度时,就是高峰。它之所以没被人们认作高峰,不是它自身高度不够,而是它自身体量太大,它的高处可容人们周转的空间太多,以至于身在其中的人,没有认识到他们每日驰骋的高原就是他们一心向往的高峰。这种高峰隐秘在自身高度与巨大体量的现象本身,也是赵望云艺术价值并未被充分认知的当下现实。由于这一点,日前中国美术馆主办的赵望云作品展,便具备了艺术史新发现的学术意义。
(作者为陕西美协理论委员会副主任、批评家)
 手机版|
手机版|

 二维码|
二维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