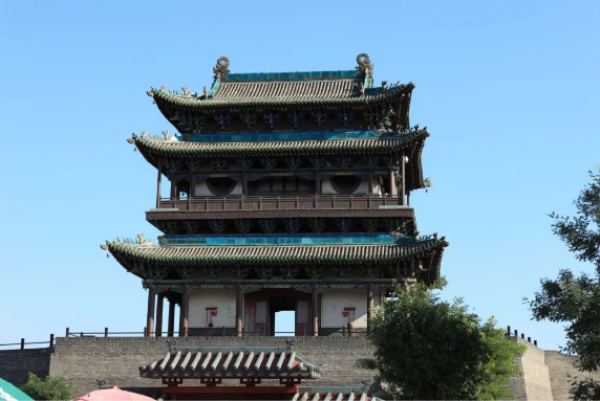秦康祥(1914—1968年)原名仲祥,后改名康祥,字彦冲,浙江宁波人,寓居上海。其曾祖秦君安、祖父秦际瀚、父亲秦伟楚三代均为在上海经商的宁波人士。幼时进冯君木先生在宁波后乐园开办的国学社学习经史文学。

合影(右坐者秦康祥)

秦康祥手拓并题
民国初年,冯君木与陈屺怀等在宁波后乐园(现中山公园)创办国学社,招生仅十余人,讲授经史文学,先后培养了冯定、冯宾符、沙孟海等名人。冯君木精通经史词章,文思敏捷,并写得一手好书法。冯先生平时治学严谨,教书育人强调“有人品才有文品”,告诫学生不能专读圣贤之书,应广学各家之文,自成风格。先生教书法也反对拘泥临帖,说临到头也不过似王羲之而已。他说习字首先要提高眼光,多观赏名人书画,博采众长于笔端,才能成器。若一味模仿,书奴也。先生更反对书法玄虚化,认为看字是欣赏,作品不是看人玩把戏。先生授徒,悉心教授且谆谆善诱。
也许适应这种私塾式的教育,上课时听冯先生讲授经史或听陈先生讲授文学,秦康祥坐得毕恭毕敬。而做笔记要求毛笔书写,于是秦康祥开始练习书法。他偶尔看到冯君木刻印章,觉得美妙无比,也用零花钱去画店买来刻刀印石,模仿老师学着刻印。听到刻石的嘎嘎声,冯君木踱过来观看,即兴指点一二,也有时接过刻刀和印石示范着刻上几刀。见秦康祥果真喜欢篆刻,冯君木说他于印艺不精,而他的同乡好友——在上海的赵叔孺十分了得,是一代篆刻名家,到时候可以为其引荐。秦康祥痴迷上了书法篆刻,买笔墨纸砚和印石就是笔不小的开支。秦康祥不敢跟父亲讨要,只能用有限的零花钱将就他无限的艺术学习。长年累月,秦康祥养成了自身节俭而购买文具十分大方的习惯,并把这习惯带入他日后的收藏活动中。
从此秦康祥的兴趣偏离了其祖辈擅长的颜料行业与钱庄生意,转向传统的文史艺术和金石篆刻。
秦康祥一生除治印外,对印学研究,收藏名印,制作印谱皆有嗜好。1943年,曾收集并辑褚德彝刻印成《松窗遗印》二卷,并题扉页,此谱有陈定山序,张鲁庵跋。1948年辑成《睿识阁古铜印谱》十册,近千方,同时辑吴泽刻印成《吝飞馆印存》一册。1949年,辑钱世权刻印成《古笛斋印谱》。1950年辑成《乔大壮印蜕》两册。又辑印谱、印学大事记,惜未成稿。他对印谱、印学之努力,给后来研究印学的人留下了一份宝贵的遗产。
秦康祥治印从师学入门,参阅先秦古玺,后以汉印为根基,故功力深厚,印风淳朴,法古而略有所变化。如“今虞琴友”一印,式仿古玺,而字之结体与用刀,似刻金凿玉,笔画细劲,结字通峭,意境深邃而幽雅,实源于古玺而具新意之佳作。
20世纪30年代初,有人将褚临本兰亭碑拿到秦家钱庄抵押。典期已到,抵押者无力赎回,碑被别人买走,流到社会。秦康祥听说后深感惋惜,从此开始追查兰亭碑的去向。直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篆刻家张鲁庵得知兰亭碑的下落,把消息告诉秦康祥。20多年的寻觅,让秦康祥受尽了煎熬。他和藏家一接触,发现果然为原物,心里暗暗高兴。像唯恐失去多年未见的老朋友一样,秦康祥价都没还就收进了。
一名古董商夹着裹得严严的包裹,神色匆忙地敲开天一阁的大门。接待他的是负责人邱嗣斌。古董商乃老江湖,深知什么样的货该送哪里。简单寒暄几句,便打开包裹得严严实实的货。里面是一幅画,画卷徐徐打开,眼前竟是征寻已久而未得见面的《鄞江送别图》……邱嗣斌按捺住心中的激动,故作镇静地俯首欣赏。待来人报出价格,他立时显得表情僵硬——这是发生在20世纪50年代末的一幕。《鄞江送别图》描绘的是清康熙十八年,清廷开明史馆,鉴于万斯同在明史研究中的成就,邀请他赴京修《明史》。万斯同“请以布衣参史局,不置衔,不受俸”,客居京师江南馆20年修史的经历深得浙东士人的敬重。画作表现的是万斯同临别时,甬上文人依依送别的历史场景。此画也是浙东学派重要的文献资料。长卷上的每个人物都有名有姓,均为当时宁波的文化名人。更难得的是,如今后人能见到的万斯同像,就出自此画,这也是大历史学家存留下来的唯一一张画像。
那时的天一阁还拿不出更多的钱来收购,可也不能眼看着这件国宝级的文物从眼皮底下消失,邱嗣斌心急如焚。情急之中他跑到上海,求助老友秦康祥关注此事。他的愿望很朴素:天一阁收不成,画作总归要落到宁波人手里。秦康祥可是古董行中的熟客,老朋友通报的信息似乎让他意识到某种责任落到肩头。打那以后,他每遇时机,都会经意不经意间询问一番,意在追寻画作下落。秦康祥执着地寻觅了几年,一次偶然的机会,终于遇到了《鄞江送别图》。他毫不犹豫地买了下来。
这只是见诸文字的收藏轶事。秦康祥收藏的文物逾8千件,许多行迹是难以言说的。
因共同的志趣爱好,秦康祥在赵叔孺家结识了比自己大40多岁的褚德彝先生,两人成为忘年交。褚德彝(公元1871—1942年),字松窗,号礼堂,学识渊博,收藏丰富,是著名篆刻家、收藏家、鉴赏家。褚德彝的晚年正逢日寇侵略上海。其时百业萧条,民不聊生,他陷入了贫病交迫的困境,秦康祥不时予以接济。及至他病逝,秦康祥又出资为他辑印《松窗遗印》。褚家后人出售藏品,其中的竹刻全由秦康祥收藏,由此可见他为人仗义,十分重友情。通过收藏,秦康祥觉得金元钰的《竹人录》仅仅收录了嘉定一地的刻竹高手。褚德彝的《竹人续录》虽范围扩大,但仍未搜尽天下刻竹艺人,他决心编撰《竹人三录》,将“两录”遗漏的刻竹家悉数入编。
20世纪50年代,每逢周日,他必带200元到广东路文物商店重点淘竹刻,兼带其它,钱要花完才罢手。200元在当时是一笔不小的款子,因为当时每人每月的伙食费才9元,鸡血石印章和齐白石的画等几十元就能买到。功夫不负有心人。十多年下来,他又收集了几十件竹刻,连同以前搜罗的,有近百件。他考证、校订、写成了《竹人三录》书稿,截止期为20世纪的60年代。《竹人三录》书稿由钱定一、郑逸梅、徐孝穆三位审定。付梓之前,“文革”爆发,《竹人三录》就此成为绝响,所幸竹刻藏品逃过一劫。
文人雅士对书斋的命名多有讲究,常常以古训、立志、寄物为寓意,可一经确定,很少改变。而秦康祥却不同。他有个习惯,也可能是太喜欢藏品的缘故,经常按照收到的心爱之物来命名书斋,使得斋名总是换来换去。收到金陵派竹刻代表人物濮仲谦刻的竹尊和嘉定派代表人物朱松邻刻的竹佛,他便将书房改为濮尊朱佛斋、竹佛斋。收进大量精美的竹刻笔筒、臂搁、扇骨、摆件后,他捧起哪件都爱不释手,于是把书斋改名为玩竹斋。后来又收到几部名琴,又改为雷琴簃、四王琴斋。再后来收藏了大量的铜印、铜镜、汉璧等,又命名睿识阁。当得到两块兰亭石刻后,他高兴得马上又改书斋为兰亭石室。叫了一段时间觉得还不够深刻,又改称唐石室。斋名不停地变,弄得好多文人雅士刚刚记住这个,等到下次来访时,又变成了另一个,多少有些摸不着头脑。这也是秦康祥收藏中的逸事。
秦康祥与王福庵也结为了忘年交。他藏书丰富,王福庵为其刻“鄞县秦氏睿识阁藏书”朱文印,边款以媲美范氏天一阁期许之,后来果然被言中。在收藏古玺印、名人字画与历代竹刻方面,秦康祥都一掷千金,王福庵评曰:“彦冲秦君,少年英俊,好金石,工刻竹,喜收藏,精鉴别,以搜罗竹刻为最富,且多可珍之品”。
秦康祥与王福庵的友情也带入了西泠印社。1951年,西泠印社由私转公,王福庵着手编纂社志。依丁辅之和王福庵的安排,秦康祥负责采访社员收集资料。接到任务后秦康祥坐火车硬座,挤公交汽车,自费往来于沪杭两地。历经八载,揽得“积稿盈寸,规模初具”。1958年春,由秦康祥出资印刷的《西泠印社志稿》面世。
1962年春,西子湖畔的柳梢刚刚吐绿,秦康祥与喜欢明清印人考订的柴子英先生和对在世印人深有研究的韩登安先生一道,相聚于西泠印社,共同商议编写印人传记之事。三人各取所长,分别拿出自己的珍贵资料,共集得3000余人。经过几个春秋的努力,终于编辑成《印人汇传》。
秦康祥毕生关心印社昌盛。与张鲁庵共同发起编拓《西泠印社同人印传》,由张鲁庵出所储石章及手制印泥,高式熊负责镌刻,印人传略则由秦康祥编撰。共得社员并与印社过从甚密者220人之多,辑为4册。
虽富商出身,可秦康祥的生活却简朴异常,除用在收藏上,其他花销能省就省。著名篆刻家、西泠印社名誉副社长高式熊回忆说:“他那么有钱,总是挤电车,从没见他坐过黄包车,也没见他请人吃过饭。”
对收藏家而言,社会动荡既是机遇,也是灾难。说机遇,是在这特殊时期,可以大量收进变卖品。说灾难,是他自己和藏品都难免受到冲击。“文化大革命”期间,秦康祥的藏品散佚严重。
2001年底,秦康祥的哲嗣秦秉年先生遵父亲嘱托,将101件(套)珍贵文物无偿捐赠给天一阁。其中的98件明清竹刻文物,经专家鉴定,有一级文物23件、二级文物59件、三级文物15件。2003年,恰逢秦秉年先生70周岁,老母亲90周岁,他又慷慨地将家藏的171件明清瓷器捐赠给了天一阁。其中,明崇祯青花人物莲子罐、清雍正豇豆红盘、清龙泉窑贯耳瓷瓶等均是罕见的珍贵文物。到了2006年11月,秦秉年再次将家藏的8000多件文物捐赠天一阁博物馆,其中一件“大富五铢”钱范属国家一级文物,此外,还有二级文物47件、三级文物1421件。
这些文物完成了一个收藏轮回后走进了公众的视野,成为了历史文化遗产。秦家由秦君安率领着走出宁波,最后由秦康祥的哲嗣秦秉年携带着全部文物重返宁波,也完成了一个家族的回归。
 手机版|
手机版|

 二维码|
二维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