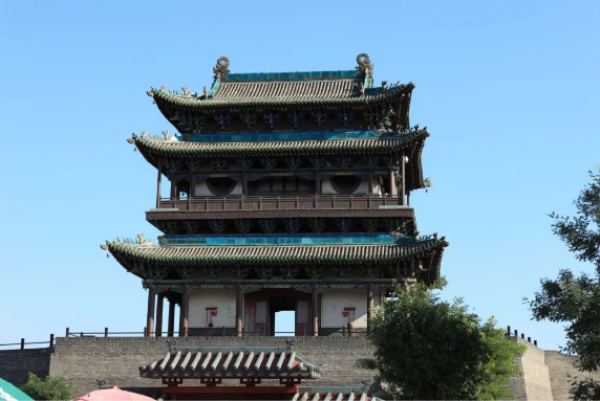侍御史是古代监察御史制度的重要一环,起源于周代的柱下史。秦代设柱下御史,西汉初期的丞相张苍即曾担任此职,两汉设侍御史。《汉书》《后汉书》对侍御史的职责有明确记载。《汉书·百官公卿表》御史大夫条:“御史大夫,秦官,位上卿,银印青绶,掌副丞相。有两丞,秩千石。一曰中丞,在殿中兰台,掌图籍秘书,外督部刺史,内领侍御史员十五人,受公卿奏事,举劾按章。”西汉时期,侍御史附属于御史大夫,但是自汉武帝确立州刺史制度后,侍御史实际上已经开始承担皇帝交给的特殊使命,并逐步走出都城,察奸治狱,护驾安民。
西汉末年,御史大夫改为大司空,侍御史不再归属大司空,而是由御史中丞统领,地位更加重要。东汉因之,据《后汉书·百官志》记载:“侍御史十五人,六百石。掌察举非法,受公卿群吏奏事,有违失举劾之。凡郊庙之祠及大朝会、大封拜,则二人监威仪,有违失则劾奏。”
《后汉书·和帝纪》注引《十三州志》曰:“侍御史,周官,即柱下史。秩六百石,掌注记言行,纠诸不法,员十五人。出有所案,则称使者焉。”侍御史的使者功能在东汉表现得更加明显,可以作为皇帝的使者,到郡国查办案件,特别是一些牵涉诸侯王的重要案件。到了汉安帝时期,由于地方盗贼频发,侍御史在督兵镇压中发挥了很大作用,如永初三年的庞雄、永初六年的唐喜,元初三年的任逴等。

现代学者的秦汉官制论著中对侍御史的监察职能着墨较多,但是对于侍御史与皇帝巡狩的关系关注较少,苏义俊《秦汉的御史官制》一文(以下简称“苏文”)通过史料排比梳理,列举了秦汉时期御史的职任,除了掌察举非法、受公卿群吏奏事,还有18项。但苏文没有将侍御史和一般御史的职责区分开来,实际上两者是有差别的。比如,苏文列举的御史第七项职任——“护从车驾巡幸,平治道路”,就是侍御史的特有职责。
护从车驾巡狩是侍御史的一项职责,但是苏文中提出的“平治道路”职责则不准确。作者是基于《后汉书·虞延传》的记载,得出侍御史具有平治道路的职责,“若道路不治,则挞侍御史。”但笔者认为这种理解显然有误。据《后汉书·虞延传》记载:
(建武)二十年东巡,路过小黄,高帝母昭灵后园陵在焉,时延为部督邮,诏呼引见,问园陵之事。延进止从容,占拜可观,其陵树株蘖,皆谙其数,俎豆牺牲,颇晓其礼。帝善之,敕延从驾到鲁。还经封丘城门,门下小,不容羽盖,帝怒,使挞侍御史,延因下见引咎,以为罪在督邮。言辞激扬,有感帝意,乃制诰曰:“以陈留督邮虞延故,贳御史罪。”延从送车驾西尽郡界,赐钱及剑带佩刀还郡,于是声名遂振。
“道路不治”指的应该是道路不平整、不好走的意思,但是从《虞延传》的记载看,当时并不存在“道路不治”的问题,而是因为光武帝车驾经过封丘县城门的时候,因为城门窄小,导致皇帝羽盖无法通过,由此惹怒了光武帝。《后汉书》对建武二十年的东巡是这样记载的:“冬十月,东巡狩。甲午,幸鲁,进幸东海、楚、沛国……(十二月)壬寅,车驾还宫。”就这次东巡来说,鲁国应该是出发前就确定好的目的地,而从洛阳到鲁国,具体该走什么样的路线,则是侍御史的职责。《虞延传》中的这位侍御史没有履行好职责,要不是虞延主动站出来为他担责,恐怕还会受到更严重的惩罚。因此,侍御史扈从圣驾巡行,负有设计选择路线的职责,而不是“平治道路”。
元和三年,汉章帝在北巡途中曾经给侍御史、司空下过一道诏敕,可以作为另一佐证。“方春,所过无得有所伐杀。车可以引避,引避之;騑马可辍解,辍解之。诗云:‘敦彼行苇,牛羊勿践履。’礼,人君伐一草木不时,谓之不孝。俗知顺人,莫知顺天。其明称朕意。”这道诏敕意思很明白,就是让侍御史和司空在巡行过程中不要随便砍伐草木,顺应自然规律,尽量避开它们,包含了巡行路线选择和铺设道路的问题。而所谓平治道路则是“掌水土事”的司空职责。有例可证:“(元和元年八月)丁酉,南巡狩,诏所经道上,郡县无得设储跱。命司空自将徒支柱桥梁。”
侍御史扈从车驾出行的职责,还可以由以下记载得到佐证:“天子出,有大驾、法驾、小驾。大驾则公卿奉引,大将军骖乘,太仆御,属车八十一乘,备千乘万骑。法驾,公不在卤簿,唯河南尹、执金吾、洛阳令奉引,侍中骖乘,奉车郎御,属车三十六乘。小驾,太仆奉驾,侍御史整车骑。”
侍御史的这项职责很可能由“乘曹”负责。“侍御史,案二汉所掌凡有五曹:一曰令曹,掌律令;二曰印曹,掌刻印;三曰供曹,掌斋祠;四曰尉马曹,掌厩马;五曰乘曹,掌护驾。”汉桓帝生母孝崇皇后去世后,“使司徒持节,大长秋奉吊祠,赙钱四千万,布四万匹,中谒者仆射典护丧事,侍御史护大驾卤簿。”对于“侍御史护大驾卤簿”,唐代李贤引用东汉应劭所著的《汉官仪》进行了解释:“‘天子车驾次第谓之卤簿。有大驾、法驾、小驾。大驾公卿奉引,大将军参乘,太仆御,属车八十一乘,备千乘万骑,侍御史在左驾马,询问不法者。’今仪比车驾,故以侍御史监护焉。”

东汉名臣胡广的《汉制度》对于皇帝车驾制度记叙得更加详细,但是《汉官仪》也有《汉制度》没有的内容——“询问不法者”。也就是说,侍御史扈从皇帝巡狩,监察沿途郡国吏治的职能是不可偏废的,这是皇帝巡狩的一项重要功能。按照汉章帝在诏书中的说法,巡狩明显具有考察吏治的功能。“二月壬寅,告常山、魏郡、清河、巨鹿、平原、东平郡太守、相曰:朕惟巡狩之制,以宣声教,考同遐迩,解释怨结也。今四国无政,不用其良,驾言出游,欲亲知其剧易……”
东汉时期特别是安帝以前,皇帝很重视巡狩,《后汉书》本纪中仅以巡狩为名的皇帝出行就达19次,其中光武帝6次,明帝3次,章帝6次,和帝1次,安帝2次,桓帝1次。此外还有为数不少的巡行、行幸等方式,如巡行河渠,行幸长安、章陵。侍御史加入巡行队伍,为皇帝实现巡狩考察吏治的功能提供了保障。
皇帝有时也利用巡行之机,从地方郡守国相二千石中物色三公九卿等重要官吏人选。比如,建武二十年光武帝东巡后,陈留太守玉况不久就擢升为司徒,陈留督邮虞延也名气大震,很快被司徒辟举为掾属,随后又先后担任公车令、洛阳令,最后位极三公。永平三年,汉明帝到南阳,听到当地吏民对荆州刺史郭贺的歌颂后,赐他三公冕服,这是对郭贺“三公之才”的期许和对各级官吏的暗示,第二年郭贺就被征为河南尹。
侍御史在扈从皇帝巡狩过程中或者回到洛阳后,还有被擢升和赏赐的记录,《后汉书·循吏传》有两条记载:“(王)景三迁为侍御史。十五年,从驾东巡狩,至无盐,帝美其功绩,拜河堤谒者,赐车马缣钱。”汉明帝因为王景治理黄河有功,在巡行过程中封他为河堤谒者。还有王涣,“永元十五年,从驾南巡,还为洛阳令”。从六百石的侍御史升迁为千石洛阳令,也属于超常擢升了。
 手机版|
手机版|

 二维码|
二维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