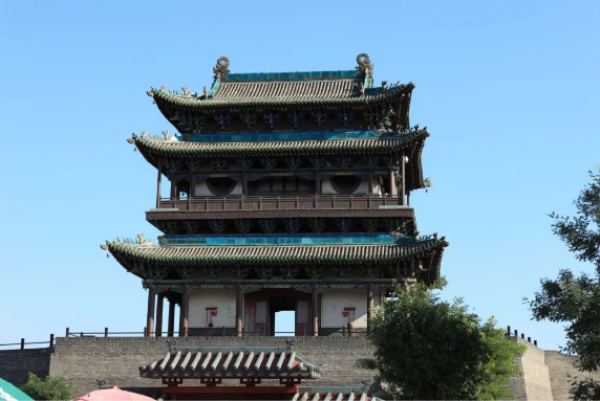庚子至辛亥期间,随着新政尤其是预备立宪的开展,清政府不断加强中央集权措施,地方督抚干政的影响力呈现减弱的趋势。然而,清政府中央集权的实际效力也并不显著,随着统治集团内部矛盾的激化反而有削弱之势,中央集权可谓有名无实。这样,便形成“内外皆轻”的权力格局。
“内轻”方面
从“内轻”方面而言,清政府虽然努力加强中央集权,但并没有建立强有力的中央政府,也未能真正控制全国的军权与财权,中央集权有名无实。
载沣摄政以后,便自代宣统皇帝为全国海陆军大元帅,任其胞弟载洵为海军大臣、载涛为军谘大臣,试图抓住军权,同时调整各部院大臣,多以皇族亲贵充任。此举激起了社会舆论的普遍反对。据英国《泰晤士报》驻华记者莫理循的观察:“摄政王最近的政策极不明智,他试图加强满人的权力,结果却适得其反。他分别任命两个弟弟担任陆军大臣和海军大臣,但这两个年轻的亲王均毫无经验和能力,没有受过专业训练,因而引起了广泛的不满,受到报界异乎寻常的大肆抨击。”御史们更是群起攻击。胡思敬奏请裁抑亲贵,有谓:“夫一国之大至要者为枢务,其次为兵权、为财权,一切悉委诸宗潢贵近之手。……宠之适以害之,恐亦非诸王贝勒之福也。”胡思敬所说尚为隐晦,江春霖则直参载洵、载涛两贝勒。山东巡抚孙宝琦也奏陈宗支不宜预政,清廷上谕虽称其“不为无见”,但随即话锋一转道:“然不知朝廷因时制宜之苦衷,且折中颇有措词失当之处,著传旨申饬。原折留中。”尽管非议四起,但这些都并没有改变亲贵专权的现实。
值得注意的是,亲贵专权实际上破坏了中央集权的效力。御史胡思敬从度支部尚书载泽把持盐政的事例认为,当时所谓中央集权,其实只集于少数部臣之手,而并没有真正加强皇权。有谓:“一二喜事之徒,方且鼓煽中央集权之说,以欺朝廷。臣见祖制未堕以前,以军机处出纳王命,以六曹总持纪纲,权本集于中央。祖制既堕以后,不但中央无可集之权,即我皇上用人大柄已渐移而之下,所谓集者,盖只集于三五要人之手耳。”这“三五要人”主要是指皇族亲贵。事实上,在清廷内部,皇族亲贵之间也是矛盾重重。朝中派系林立,内耗不已,政治则无所为。
恽毓鼎认为:“劻耄而贪,泽愚而愎,洵、涛童騃喜事,伦、朗庸鄙无能,载搏乳臭小儿,不足齿数。广张羽翼,遍列要津,借中央集权之名,为网利营私之计,纪纲昏浊,贿赂公行。有识痛心,咸知大祸之在眉睫矣。”如载泽,“缘内援而参国政,削督抚兵权、财权归中央,倚任东洋留学生,建铁路收归国有政策,力庇其姊婿瑞澂,皆其主谋也。”载泽虽极力主张中央集权,但在关键时候并没有承担。时人批评:“闻泽公[载泽]遍电督抚,言路归国有,由监国[载沣]一人所持主义,伊与盛宣怀皆不知。此等举动,殊属可笑。善则归君之义,岂未闻乎?事已至此,且须图谋救败之法,若君臣相诿,何益于事。且即主义实出于监国,伊为度支大臣,所职何事,乃谢以不知耶?近传其有告病之说矣。”可见,亲贵们确实是“借中央集权之名,为网利营私之计”。
辛亥前夕,清廷面临内忧外患危机,但皇族亲贵们却醉生梦死。“现在政府诸公仍在梦中,政出多门,贿赂如故,宫中三体,各怀意见,满与汉既分门户,满与满又分界限,京外又有畛域,中外又有猜嫌。国病如此,虽有医国手数辈,亦无能为力,何况竟无一人也。可叹可怕!”无论是摄政王载沣与隆裕太后,还是庆亲王奕劻与载泽等亲贵,都不是“医国手”的强力人物,无法挽狂澜于将倾,拯救垂死的清王朝。
其实,监国摄政王载沣在预备立宪时期实行的中央集权措施,既没有建立强有力的中央政府,也未能真正控制全国的军权与财权,反而使国家军力脆弱,财政匮乏。这可以武昌起义后清廷尴尬局促的应对为证。
清廷通过中央集权,把新军的指挥权、调遣权收归军谘府、陆军部,但事实上,军谘府、陆军部并不能有效地指挥和调遣新军。武昌起义之后不几天,清廷便从近畿与北方各镇新军中抽调部队,有梯次地编配三军:第一军进攻前线,第二军预备待命,第三军防守近畿。上谕称:“现在派兵赴鄂,亟应编配成军。著将陆军第四镇暨混成第三协、混成第十一协,编为第一军,已派荫昌督率赴鄂。其陆军第五镇暨混成第五协、混成第三十九协,著编为第二军,派冯国璋督率,迅速筹备,听候调遣。至京师地方重要,亟应认真弹压,著将禁卫军暨陆军第一镇,编为第三军,派贝勒载涛督率,驻守近畿,专司巡护。该贝勒务当妥慎筹备,加意防维,毋稍疏虞。”应该说,清廷最初的这个反应不可谓不相当迅速,但实际执行情况则完全不尽如人意。清廷抽调编配三军的部队主要是北洋新军的精锐,而北洋新军由袁世凯编练而成。关键的问题就在于此。袁世凯曾在北洋军中遍布党羽,“近畿陆军将领以及几省的督抚,都是袁所提拔,或与袁有秘密勾结”。他们只知袁宫保,而不知清朝廷。即使袁世凯被摄政王载沣罢黜回籍,但他“仍在暗中操纵一切”。

袁世凯
在清廷编配的三军中,第三军奉命防守近畿且不说,还有预备待命的第二军因滦州兵变事实上并未组成,单说那调拨前线的第一军,该军虽由陆军大臣荫昌直接督率,但并不能如意指挥。“荫昌督师,在当时已有点勉强,荫虽是德国陆军学生,未曾经过战役,受命后编调军队,颇觉运掉为难。其实此项军队,均是北洋旧部,人人心目中只知有‘我们袁宫保’”。荫昌虽出身德国留学生,并贵为陆军大臣,却不能自如指挥新编第一军,因为这是袁世凯的“北洋旧部”。于是,在各方面“非袁不可”的背景下,清廷被迫起用蛰伏多时的袁世凯。袁世凯随即奏请改派心腹旧将冯国璋为第一军总统,段祺瑞为第二军总统,得到清廷批准。随后,清廷召回陆军大臣荫昌,授袁世凯为钦差大臣,并谕令:“所有赴援之海陆各军,并长江水师,暨此次派出各项军队,均归该大臣节制调遣。……此次湖北军务,军谘府、陆军部不为遥制,以一事权。”可见,至少在武汉前线,军谘府、陆军部已经被迫自动放弃了军权,其所谓中央集权竟是如此脆弱,这大概非清廷始料所及。
至于财权,皇族亲贵载泽执掌度支部时,曾极力主张中央集权,以收束地方财政权力。但是,由于亲贵们争权夺利,往往借集权之名,而行搜刮财富之实,中央财政并无起色,反而前途甚堪忧虑。时人批评:“现时部中之经济,只知夺商办已成之利,攫各省已有之财,未见之利源则不知开辟,未成之商业则不予维持,仅新美其名曰中央集权、统一财政,因应如是也。不知中国膏脂将已吸尽,若不赶紧于路矿实业等事举办,恐不到九年预备,已有束手之势。”“以后中国筹款办事日难一日,官吏既不敢独任,舆论又言不顾行,官绅商民喧攘纷争,不知伊于胡底。国内乱起,外侮又乘之而入,在土崩瓦解之时代矣。”真可谓不幸言中。
武昌起义后,清政府国库空虚,筹集军饷非常困难。据署理度支大臣绍英日记载,当时度支部库实存现银9871万余两,辅币74万枚。绍英“竭蹶从事,艰窘异常。倘借款无成,实无善策。闻内帑尚有存储,第讨领不易,不知将来能办到否?”隆裕太后召见内阁总理大臣袁世凯商议和战大计与政体抉择时,老练的袁世凯以四两拨千斤的方式提出关键的军饷问题,直击清廷软肋,有谓:“政体本应君主立宪,今既不能办到,革党不肯承认,即应决战,但战须有饷。现在库中只有廿余万两,不敷应用,外国又不肯借款,是以决战亦无把握。”事实上,至少在财政上,清政府确实已没有决战的资本。袁世凯正是利用此点而挟持清廷,与革命党讲和。
其时,前方各路清军将领及各省督抚纷纷电奏,恳请王公亲贵毁家纾难,捐献私产。清廷“谕令宗人府,传知各王公等,将私有财产,尽力购置国债票”,但所得无几,杯水车薪,无济于事。据郑孝胥记载:“宫中存款已尽出,约九百万两,可支至十二月初旬耳。亲贵私蓄二千九百万,皆不肯借作国债,惟庆邸出十万而已。虽谓亲贵灭清可也。”又据许宝蘅记载,隆裕太后召见袁世凯时,又谕:“‘现在宫中搜罗得黄金八万两,你可领去用,时势危急若此,你不能只挤对我,奕劻等平时所得的钱也不少,应该拿出来用。’总理对:‘奕劻出银十五万。’太后谕:‘十五万何济事,你不必顾忌,仅可向他们要。’”袁世凯甚至以“库空如洗,军饷无著”为由,上奏“请将盛京大内、热河行宫旧存瓷器,发出变价充饷,以救目前之急”。清廷被迫允准。可见清廷财政已处捉襟见肘的无比艰难窘境。署理度支大臣绍英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感触颇深,有谓:“计自暂署度支大臣两月,筹款维艰,智穷力竭。现在虽库款尚敷一月之用,而军用浩繁,终有饷项难继之一日,愧悚奚如。”他深感实在是无力回天,不得不托病请假,并奏请开缺。如同军权一样,清廷在财权方面实行中央集权的实际效力也是微乎其微。
“外轻”方面
从“外轻”方面来说,就是地方督抚权力被收束而明显削弱,在地方已没有强势督抚,也不能有效地控制地方军权与财权,没有形成强大的地方势力。
在清末新政与立宪的过程中,清廷加强中央集权,有意削弱地方督抚权力,也曾遭到地方督抚的抗拒。如两广总督岑春煊,曾力陈中央与地方相互维持之道,认为地方督抚权重亦不可削弱。他说:“中国各省辄藉口于因地制宜之习惯,于是彼一是非,此亦一是非,论者不揣其本,更托为中央集权之说,欲收一切财政、兵权,以为暗师日本削藩之议。不知中国幅员固非日本所可比例,且军兴以来,督抚之权似已稍重,然进止机宜,悉秉庙谟,大难敉平,幸赖有此。中国政体早含有中央集权之习惯,天下更安有无四方而成中央者哉。恭绎列朝圣训,于治臣御侮皆注重疆臣,以矫宋明重内轻外之弊,近如英之属地,美之各省,亦不能不委重权于驻守之臣及一省之长,更可证四方之与中央有相为维持之道也。”又如东三省总督锡良,则对于中央集权的祸害深表忧虑,有谓:“至于今日所最忧者,尤为中央集权一事。主是说者,鉴于外人讥我二十二行省为二十二小邦之说,思欲整齐画一之,意非不善。不知中央集权之制,揆诸中国历史及地理上各种关系,断难尽适于用,即西人亦能言之。”尽管岑春煊、锡良等督抚如此极力抗争,但他们还是没能改变清廷中央集权的既定路线。
清廷通过新政与立宪实行中央集权的结果,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地方督抚的权力。资政院议员于邦华尖锐地指出,地方督抚无权办事的症结,就是清廷实行中央集权措施所致。御史胡思敬则从中央集权使各省“都成散局”的严重后果,论证新政足以招乱,有谓:“自中央集权之说兴,提学使为学部所保之员,巡警道为民政部所保之员,劝业道为商部所保之员,皆盘踞深稳,不敢轻言节制。而又司法独立,盐政独立,监理财政官气凌院司,亦骎骎有独立之势。一省之大,如满盘棋子,都成散局。将来天下有变,欲以疆事责之督抚,而督抚呼应不灵;责之学使以下各官,而各官亦不任咎。”这并非危言耸听,武昌起义之后地方督抚无力效忠朝廷的惨痛事实即为明证。
清末地方督抚权力削弱的表征有二。
一是没有强势督抚,也没有形成强大的地方势力。在清末新政时期,除直督袁世凯与鄂督张之洞任期较长以外,其他地方督抚任期多短暂,且调动频繁,较少久任督抚。据统计,其时总计有119个督抚,任职在2年以下者占80%以上,其中总督任职在半年以下或未到任者占551%,巡抚占494%,各省督抚调动频率大都在一年一次以上。督抚更调频繁,使政策的稳定性大打折扣,对地方政治颇为不利。光绪二十九年(1903)四月初五日,慈禧太后在召见四川按察使冯煦时称:“督抚确有一种毛病,好变更前任的事。”冯煦答:“不独尽弃前任的事不可,即不明变,而视为前任之事,不甚著力,属员亦窥伺意旨,相率因循,使前任苦心经营之事不废而废,最为可惜。”但与此同时,督抚更调频繁,也不容易形成地方势力,而有利于中央对地方的控制。著名督抚如袁世凯、张之洞、岑春煊、端方,是李鸿章、刘坤一去世之后最有影响的地方督抚大臣。在清末新政十余年间,岑春煊任督抚9次,端方11次。尽管岑与端也可谓当时难得的干才,但因过于频繁调动还是难有作为,也不可能在某处扎下固定的根基,其他平庸之辈更可想而知。任期长者如袁世凯、张之洞,其实也没有形成地方势力。清廷始终紧握对地方督抚的任免权。袁世凯虽久任北洋,并与庆亲王奕劻勾结,曾一度权倾朝野,但很快引起清廷警觉,其权力不断被削弱,终归被罢黜回籍。张之洞虽在湖北经营近18年,但一朝离开湖北后,湖北立刻大变,其继任者赵尔巽全改其制度。张之洞曾对袁世凯抱怨:“君言我所办湖北新政,后任决不敢改作。试观今日鄂督所陈奏各节,其意何居?且其奏调各员,均非其选,不恤将我廿余年苦心经营缔造诸政策,一力推翻。”可见湖北并不是张之洞永久的势力范围。宣统元年(1909)十月,直隶总督端方被黜,许宝蘅日记称:“匋帅在近日满汉大臣中最为明白事理,器局亦颇开张,虽所为不足满意,然亦不易得,今又被黜,益增无人之叹。”其时,张之洞已去世,袁世凯、岑春煊都被迫在野,端方又遭罢黜,环顾宇内,确实已没有强势督抚。到武昌起义前夕,如直督陈夔龙、江督张人骏、鄂督瑞澂等,都是与袁世凯、张之洞等人不可同日而语的平庸之辈,地方督抚并没有形成尾大不掉的地方势力。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这大概就是中央集权的效力。
二是各省督抚不能有效地控制地方军权与财权,使地方军心涣散,财力竭蹶。这也可以武昌起义后各省软弱无力应对为证。清廷为实现中央集权,把各省新军的指挥权、调遣权统归军谘府、陆军部,削去地方督抚的兵权,是最为致命的。武昌起义之后不久,御史陈善同一针见血地指出:“各省督抚,膺千余里土地之重寄,为数千万人民之所托命,万不可无调遣兵队之权,以资震摄。苟既命以如此重大之任,而复靳兵权而不予,是不啻缚其手足而使临民上,欲求无事不可得也。疑其人而罢其督抚之任可也,任之而复疑之,缚其手足不可也。今各省会城之变,大抵皆坐此弊,则兵权集于中央之说误之也。……今则各省陆军皆一律归部直接管辖矣,各该督抚均不能直接调遣矣,若不速为变计,乱未已也。”
各省新军名义上归地方督抚节制,但实际上督抚很难调动新军。如湖广总督瑞澂,在武昌起义之后极力剖白,事变由“新军应匪”而起,并特别申明“陆军为统制专责”,统制张彪无法控驭,而巡防队又迭次裁撤,所剩无多,且分防各府州县,以致武汉兵力奇缺,“瑞澂以孤身处于其上,无从措手”。又如湖南巡抚余诚格,得知新军谋变,遂与司道及巡防队统领密谋,“将新军分调各府州县驻扎,以散其势”,但新军并不想动。“余诚格迭催新军开赴各属,各新军乃藉口子弹不充,请加发三倍,方能应调。余诚格不允,遂相持不下”。随后新军便在长沙起义。武昌起义由新军发动,各省响应者亦多为新军,地方督抚遂对新军避而远之。如两江总督张人骏所谓:“陆军名誉被鄂事牵累,不能用而反应防。各省情形,如出一辙,此间尤甚。”“糜无数金钱,久经训练之陆军,几等养虎自卫,可胜浩叹!”因新军不可靠,而巡防队又不敷调用,“宁省巡防止三十余营,分防至千余里之遥,零星散扎,均难仓卒抽动。浦口防军虽系长江游击之师,惟因事先后调往皖、苏各省及徐州等处已居多数,亦难一时调集。至赣、皖、苏各省兵力,更形单薄。下游地段绵长,非现有防营足敷防守”。张人骏奏请参照从前湘军营制,添募十营,名为“巡防新军”。军谘府、陆军部指示宜照章参用陆军教育,并“希勿用巡防新军名目”。张人骏只得遵照改称“江南巡防选锋队”。军谘府、陆军部竟然忌讳“新军”之名,颇可玩味。清政府在推行新政的过程中,在编练新军的同时,正逐步裁减绿营、巡防队等旧式军队。此时,为应对危局,陆军部奏请各省绿营、巡防队一律暂缓裁减,以辅陆军、巡警所不及。清廷允准:“所有宣统三年预算案内,各省奏明碍难裁减之绿营、巡防队,均著免其裁减;并四年预算,除直隶、江、赣等省仍照奏准各案办理外,余著一律暂免裁减。”然而遗憾的是,在新军一片倒戈的形势下,依靠旧式军队绿营与巡防队,并不能阻挡住各省纷纷独立的势头。
至于地方财政,其捉襟见肘程度与中央财政相比,可谓有过之无不及。两江总督张人骏所在江南地区,本是财赋裕足之地,但亦“库帑如洗”。张人骏不停地诉苦,有谓:“鄂乱事起仓卒,江南地处下游,向多伏莽,窃发堪虞。皖、赣逼近鄂疆,兵备均甚空虚,非缓急有备,实难肆应。即军队抢[枪]械,亦当预筹添购,米粟并须储峙,在在需款。……欲济眉急,舍息借别无办法。”于是拟借洋款五百万两,后又拟加借二百万两。又谓:“江南财政困难,至今已极,实无可移之款,息借之外债经分别抵还,已所余无几。即人骏所招之十营,亦尚在筹措前项勇饷。”于是又恳请度支部筹拨的款一百三十万两。事实上,不但部拨的款难有指望,息借洋债更无着落。张人骏几近绝望,“欲支危局,先求足用,帑项告竭,瓦解即在目前”。
江南如此,其他各省更是竭蹶不堪。各省督抚纷纷向清政府请拨的款,或奏请息借外债,使清政府应接不暇。陕甘总督长庚等致电内阁、度支部称:“宁夏失陷,土匪四起,藩库存饷仅支一月,有支无收,危急万状。惟有泣求钧阁部,速济的饷百万,由归绥、迪化分起汇解,以救倒悬。”又电内阁称:“比款既难划出,所有原议借三百五十万,即全归甘省担任。……乞速照会比使订借汇解,以济急需。”山西巡抚张锡銮电称:“晋省乱后,库空如洗。除不急之务暂停办外,目前紧要军警兵饷及善后急需,至少非有百万不办。日前请领二十万,望饬速发,以济眉急。”直隶总督陈夔龙电奏:“津市危迫,饷需万急,饬交涉使与各洋行商借银二百万两,一年归还,以本省各实业官股及烟酒税作为虚抵。”清廷允准其向各洋行商借,以济要需。
当清廷以部库空虚,要求各省筹饷接济时,东三省总督赵尔巽称:“奉库久罄,两月以来,全赖维持纸币,赖以支住,断无现款拨供汇解。”吉林巡抚陈昭常称:“吉省库储支绌,现币无多,全赖官帖周转。两月以来,添兵购械,所需至巨,均系勉力支持。如饷项稍亏,亦虞哗变,危险即在眉睫。现在全省绅民,对于财政监察甚力,即有现款外运,势必全力抵抗。加之人心浮动,讹言孔多,倘因而生事,祸患之迫,何可胜言。再四思维,实无他法。”据统计,宣统三年(1911),各省预算案内本来就有很大的财政赤字:不敷在一百万两以内者,有吉林、黑龙江、山东、山西、河南、甘肃、热河等省区;在一百万两以上者,有贵州105万,江苏108万,安徽、福建各115万,广西137万,湖南157万,云南193万,江西254万,湖北539万,四川774万。战乱突发,旧式军队绿营、巡防队暂缓裁减,还得招募新兵,军费急剧增加,使各省督抚焦头烂额。地方财政已到崩溃的边缘,面对革命风暴,地方督抚无力应对也就不足为怪了。
可见,正是地方督抚权力明显削弱,而清廷中央集权尚未强固之时,即在此权力转换临界的关键时刻,武昌起义爆发,这无疑是对清王朝的致命一击。清末“内外皆轻”权力格局的表征在武昌起义之后非常明显:一方面,清廷没有建立强有力的中央政府,也未能真正控制军权和财权。陆军部大臣荫昌不能指挥武昌前线的北洋新军,而不得不重新起用旧臣袁世凯。同时国库空虚,而度支部又无法筹集军饷。另一方面,在地方已没有强势督抚,其军权与财权均大为削弱。独立各省督抚既无法控制新军,也不能筹集军饷,大都成为无兵无钱的光杆司令,只能消极应对革命形势。因此,清王朝便无可挽救地迅速走向土崩瓦解。
值得进一步说明的一点是,当清廷中央与地方督抚的权威一并衰落之时,军人势力崛起,从而出现军人干政局面。后来,袁世凯正是依靠新军的力量,进入清廷权力核心,从中央而不是从地方控制清政府,从而攫取清朝政权和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这是军人干政发挥到极致的典型事例,而不是地方势力膨胀的结果。民初北洋军阀并非清末地方督抚,而多为清末新军将领。例如,冯国璋、段祺瑞起初并没有地方根基,只是因掌握大量军队而控制相应的地盘而已。即便是阎锡山、张作霖,也是以军人身份乘乱而起,以武力称雄,割据一方。北洋军阀的起源并非地方势力的兴起,而是军人以武力控制地方的结果。那种认为由清末地方势力直接蜕变为民初北洋军阀的观点,纯粹是与历史本真不相符合的逻辑推演。事实上,在清末武昌起义之前,并没有强大的地方势力,也没有地方主义抬头,所谓地方势力或地方主义,毋宁说是民初军阀政治的表征。职是之故,从军人势力的崛起与军人干政的角度,探究民初北洋军阀的起源与军阀政治,或许是一条更理想的路径。
 手机版|
手机版|

 二维码|
二维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