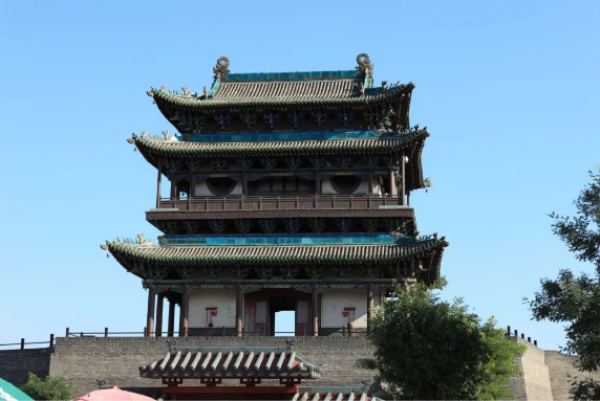徽州古民居,既是中原文化与山越文化相结合的产物,又是儒释道多家文化的结晶,传统文化意味十足,但其中蕴藏着新变的理念。这主要体现为:楼居方式是干栏式建筑与中原建筑文化的融合;在型制上是因地制宜和而不同的展现;在风水上改风改水为徽人服务;在色彩上蹊径独辟追求至高的人生境界;天井的设置是北方四合院在徽州的转型;小部件斗拱有着独特的象征意味。
法国作家维克多·雨果曾说过,人的思想就像宗教一样也有其纪念碑,这就是建筑。徽州古民居,是中国传统建筑的杰出代表。1999年12月,皖南古村落西递、宏村入选世界文化遗产名录。世界遗产委员会这样评价:“西递、宏村这两个传统的古村落在很大程度上仍然保持着那些在上个世纪已经消失或改变了的乡村的面貌。其街道的风格,古建筑和装饰物,以及供水系统完备的民居都是非常独特的文化遗存。”
徽州在历史上是个移民社会,中原的精英人士南迁后,汲取了中原和土著的文化精华,彰显出巨大的包容性和创造性。徽州古民居体现了儒家、道家、释家等多种文化的交融,“涵义最完美的建筑历史,几乎囊括了人类所关注的全部事物。”徽州古民居是在农业文明的基础上,加上徽商文化的传统凝聚而成的,其间渗透着新变理念,具体体现在以下六个方面。

楼居:干栏式建筑与中原建筑文化的融合
徽州的土著居民为山越人,在长期的生活中积累了丰富的生存经验。他们在山间潮湿、多雨的亚热带气候环境中,采取干栏式建筑模式——楼居结构。山越文化“是开发江南山区的先民在一个相当长时间里,吸纳融会多种文化而逐渐生成的新质文化,其中包括原住民文化,吴、越和楚文化成分,甚至包含良渚文化若干因素”。良渚文化的房屋以木构为主。干栏式木楼为穿斗式木结构,木材从当地的山中就地取材,一般为杉木,房屋的开间不大。西晋的永嘉之乱、唐代安史之乱、北宋靖康之变,中原地区战事频发,民不聊生,北民大举南迁,徽州山高多屏障,如世外桃源一般,成了北民避难的胜地。南迁的居民,带来了先进的中原农业技术,也带来了先进的建筑文明。当先进文明融入到后进文明后,发达的中原文化很快就反客为主了。北方的合院采取抬梁式架构,用材粗大,开间也比较大。徽州民居楼居式的结构,大多采用两层楼,也有少数三层楼,有的在地面上铺设木地板,用来通风隔潮湿,避免湿气直接对人产生影响。徽州民居“汲取了干栏楼居开敞的堂屋和挑台特征,将正中厅堂扩大并半敞开,与天井空间连成一片”。在厅堂部分采取抬梁式结构,空间的跨度较大;在空间较小的卧室则采用穿斗式结构。
中原地区农业文明发达,长期为政治文化中心。其建筑文化以北方官式建筑为基础,强调儒家的伦理道德秩序。到了徽州后,徽民重视宗祠建设,维护同一氏族的权威,在建筑中体现等级化,甚至直接用门联、匾额体现封建的伦理秩序,广设牌坊标志。诸多的建筑形式,都能体现出中原建筑文化重伦理的痕迹。在传统的男耕女织的农业社会里,女性在家庭中是没有地位的,男性是家中的家长,是家中的绝对权威。就民居空间的使用来说也是如此,严格的女教观念使妇女的活动区域很小,大户人家的女孩在出嫁前都是“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在阁楼里终日学习女红或者抚琴作画。闲暇的时候,也只能待在美人靠边欣赏室内的风景。

型制:因地制宜、和而不同的展现
徽州山多地少,人口多,可耕地较少。在为数不多的平地上建造房屋,宅基地显得比较局促,民居的建筑布局紧凑。加上明朝时期,皇家对建筑的规定很多,住房的等级也会根据官员的级别不同有所差异。明朝对建筑规定森严,据《明史·舆服志》记载:藩王称府,官员称宅,庶人称家,住宅建造大小亦受限制。王侯、官员按等级造房,庶人只能造“三间五架”之屋。
徽州民谚有言:“前世不修,生在徽州,十三四岁,往外一丢。”徽州人多地少的矛盾,刺激了徽州重商的传统。徽商在明清之际,驰骋中国商场几百年,甚至有“无徽不成镇”之说,可见徽商的足迹遍布中国;徽商的繁荣极盛,富可敌国,可见当时徽商的影响力。发迹后的徽商回到家乡买田置地,荣归故里,大兴土木,建造了很多的民居建筑和祠堂、牌坊、书院等公共建筑。虽说地处山高皇帝远的徽州,但皇家对建筑的规定徽商是不可违背的,只有另辟蹊径,在新变上做足文章。
在山光水色的映衬下,徽州古村落宛如“中国画里的乡村”,魅力四射,韵味无穷。从外观上来看,青砖、黛瓦、马头墙,这是徽州民居的共性之处,但具体到每一家每一户,又会根据宅基地的大小、地形、地势,结合主人的个性和审美追求,呈现出不同的风貌。穿行于徽州民居间的小巷,置身其间,经过每家每户,从门楼到房屋的装饰,找不到完全相同的两户,这就是徽州民居的独特之处,也体现了中国文化的“和而不同”。
风水:改风改水为徽人服务
徽州民居追求“枕山、环水、面屏”,形成枕山环水、依山傍水、背山面水的格局。在徽人眼中,理想的村址是符合风水观念的,要遵循“阳宅须教择地形,背山面水称人心,山有来龙昂秀发,水须围抱作环形,明堂宽大斯为福,水口收藏积万金,关煞二方无障碍,光明正大旺门庭”。徽人重视风水由来已久,赵吉士在《寄园寄所寄》说:“风水之说,徽人尤重之,其平时构争结讼,强半为此。”王明居先生认为:“风水,就其存在状态而言,是客观的。它是大自然的产物,因而有它的自然性。具体地说,它是特定时间、空间中的自然山水风貌,是建筑所处的自然地理环境。风水本身是独立于人的意识之外的客观存在,它是没有意志的。但是,风水观念却是人对风水的认识,因而是主观的。我们绝不可把风水与风水观念混为一谈,把客观与主观混为一谈。”
徽人在建造房屋的时候,遇到风水不符的,就得改风改水。比如徽州的风水镇符石敢当。石敢当为长方形石碑,通常被置于村落入口处、河流池塘岸边、门前巷口、三叉路口直冲处等,有的镶嵌在墙中,有的独立放置。歙县渔梁某宅因门正对紫阳山上一怪石,故将门偏斜朝向紫阳峰,同时在门前立“泰山石敢当”。黟县城内很多民宅将门远离冲巷处,而在直冲巷子的墙角处立一块“泰山石敢当”。
徽州很多村落四面皆山,形成相对封闭的空间。水口是进入村落的咽喉,在村民眼中水口关系到村落人丁财富的兴衰聚散。为了留住财气,除选中好的水口位置外,还必须建筑桥台楼塔等物,增加锁钥的气势,扼住关口;同时也改善了村落的环境及景观,形成“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的村落总体环境特征,使水口成为徽州的村落庭园。除了水口林,还有根据风水“障空补缺”理论的需要,建造文昌阁、奎星楼、庙宇等建筑,改变徽州的风水为徽人服务。

色彩:蹊径独辟中的至高追求
明清时期的建筑装饰用色,有着深刻的等级观念,王公、大臣与庶民在建筑上的差异很大。北京故宫等宫廷建筑光彩照人、金碧辉煌,大多采用黄色、红色、金色进行装饰,红色代表神权,黄色昭示君权,充分体现出神权和皇权的至高无上,呈现出一种“错彩镂金”之美。
徽州古民居,是徽商出资建造的。受等级森严的建筑制度的影响,建筑装饰只能避开“错彩镂金”之美。徽商的活动区域很广,并且多在外乡经营,在家乡采用低调的色彩可以确保家乡的财产安全。加上程朱理学对徽州影响深远,朱熹主张平淡自然,在色彩上倾向于中和的无彩色,生活在山水之间的徽民逐渐造就了徽州民居清新、淡雅、洁净的建筑风貌。在色彩的选择上,人们喜爱色度偏低、色调中性的调和色,用黑、白、灰作为主色调,加上与青山绿水协调一致,给人以“出水芙蓉”之美。“在中国传统观念中,白色具有多向性,表示光明之源,在徽州许多建筑中高耸延伸的白墙几乎与浅色天空连成一片,追求真正的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黑色则象征天,它源于夜幕之神秘;而青灰色则与五行中的水相对应,寓意着避免水灾。”
天井:北方四合院在徽州的转型
中原土地平坦辽阔,宅基用地相对充裕,民居采用宽敞的四合院院落式建筑,随着中原士族的南迁,到了土地紧缺的徽州,没有足够的土地建院落,阔大的四合院变成了建筑物内部的天井。这一转型前后,基本的精神还是相通的,就是住宅的自然化,充分体现了古代的天人合一的观念。所谓住宅的自然化,就是把室外的空间“借”到室内来,天井是建筑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这是因为营建者受到传统生命哲学的深刻影响,认为人与自然是血肉相连、同心同构的。
徽州的天井,除了有采光、形成小气候等功能外,还是连接大门与厅堂的中介。厅堂是全家人的中心活动区域,也是会客的主要空间。坐在厅堂内,通过天井可以感受到四时之变,阴晴圆缺,云卷云舒,晨淋朝霞,夜观星斗,不仅可以安顿性灵,还能愉悦情性。室内空间的有限,通过天井走向了无限,个人心中的小宇宙与天地的大宇宙连成了有机的整体。正如张世英先生所说:“每一物、每一人、每一部分、每一句话、每一交叉点都是一个全宇宙,但又各有其个性,因为各自表现了不同的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方式,或者说,各以不同的方式反映了惟一的全宇宙。”[7]在这种相通之中体现生命或者生活的意义与价值。
徽商长年在外经商,财源来自四面八方,希望图个吉利。水主财,故而“四水归明堂”。天井四周的屋顶坡面,东西南北四面的雨水通过小青瓦流入家中,意味着肥水不外流,象征着财气的汇集。这种对应关系,也是徽派古民居营建者心理的折射。
天井是虚实的统一体。天井可以分为井口、井身和井底三部分,井口和井底是可视的,是有形的实在,井身是不可视的,是无形的虚空,但正是这虚实的结合,才成为徽州古民居中独特的天井的结构。这种虚实相生,实现了生命的超越。虽在厅堂之内,心系浩渺宽广的宇宙时空,使居者不囿于厅堂,而是通过天井实现与天地宇宙的合二为一。主人在堂前玩味天井,独享人生的快乐。宗炳的《画山水序》认为,在“澄怀味象”中,最终“万趣融其神思”,审美主体在“畅神”中获得了物我的根本同一。
斗拱:小部件呈现的象征意味
斗拱在中国建筑技术中是一大创造,是作为承重构件而产生的。“它一般总是出现在较大型较重要的建筑物上,久而久之,便成为社会权贵、统治者政治伦理地位、等级与品格的建筑象征。发展到封建社会的中后期,便只有宫殿、帝王陵寝、坛庙、寺观及府邸等一些高级建筑才允许在立柱与外檐的枋处安设斗拱,并以斗拱层数多少,来表示建筑的政治伦理品味。
徽州的如意斗拱呈现出吉祥意味,是中国传统斗拱之美的积淀与升华,有着徽州工匠的独创性。一方面起到负重的作用,还有着突出建筑磅礴气势的审美作用。斗拱部件单纯,组合明朗,但结构复杂,多样统一。“它以绚烂多姿、五彩缤纷的藻饰涂抹造型,使它那简洁的构架形式又增添了繁缛的色泽与光辉。”
“徽州人在建造斗拱时,还能因地制宜,在宁静、寂寞、偏僻的山水之间,既显示出斗拱的隐秘性、深邃性,又突出它的流动美、峻拔美。同时,为优美的徽州建筑增添壮美,为优雅的山区注入活力,使青山绿水显得更有生机。”这与北方不同,北方的平原区域,没有青山绿水的映衬,斗拱显示出的则是雄浑豪放之气。
梁思成先生曾说:“建筑之始,产生于实际需要,受制于自然物理,非着意于创新形式,更无所谓派别。其结构之系统,及形式之派别,乃其材料环境所形成。”艺术创造不能全部脱离以往的传统基础,总是在基础之上进行创新,在徽州古民居中,多种文化的交融与渗透,形成了独特的古民居样式。创新,是民族的灵魂。这些新变的理念进而转化为徽州古民居的现实构造,是徽州匠人的创造,也是徽商的创造,更是中国传统文化在自身内部的创新,值得我们深思和总结。
 手机版|
手机版|

 二维码|
二维码|